人间烟火|陶醉荥家湾
朗溪甘川,印江十二宴席之土司宴菜品展示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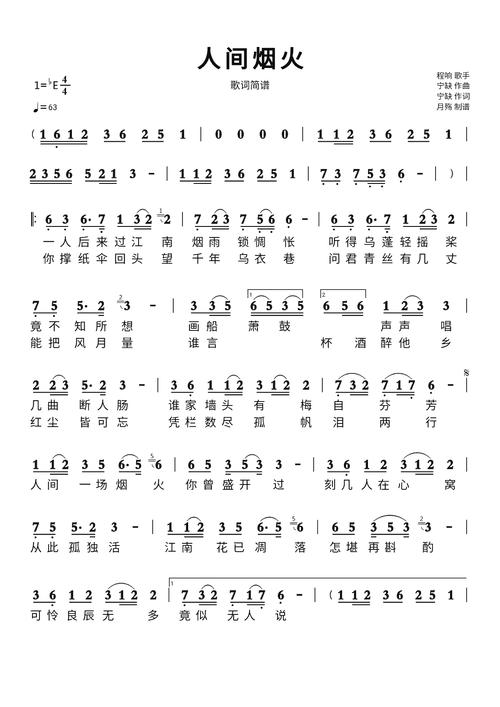
院坝中间的一张大圆桌上,各式菜肴在清凉的晚风里冒着腾腾热气,奉着袅袅异香萦绕鼻端。本来闲散着的师友们,突然间像被一股磁力牵扯,一下子就把圆桌严严实实围住,嘴里啧啧有声,喉结不自觉上下汩汩滑动,一双双眼睛逐一扫描,最后不约而同聚焦于一只汤钵里的公鸡。但见鸡头昂然,鸡冠竖立,鸡身雄踞,在它周围有点点红绿浮泛,一层薄薄的油光在夕阳余晖的反射中泫然荡漾。大红的是枸杞,深红的是大枣,绿的是葱花,白的是蒜片,黄的是姜沫儿——异香之源,便始于这里了。乍一看,这公鸡似巡游的将军一般趾高气扬,而他的车辇,是一个一尺来高的略泛土黄色的器皿,古朴,稳重而又厚拙——“这叫鸡甑”,旁边有人介绍,“本地加工,是一种专门用来清蒸鸡肉的窑罐。”于是,这场土司宴后,脑子里被牢牢镌刻了四个字:本地陶器。
清晨,山里的空气略带薄凉,半山腰里烟岚飘渺,如在蓬莱。我们驾车出县城,在朗溪街上朝右拐上一条老公路。窗外再没有高速上那种风驰电掣的景物切换,一切都慢了下来。清风摇曳,万物翩然,如一位裹着浓绿裙装的少女施施然走来,只轻引素手,我们便被她牵着走向大山,走向时间的深处。
乡村连户路若蛇形斗折,一直蜿蜒至半山那个叫荥家湾的偏僻小村落。车刚驶上一处平台,便见前方站着一位壮实的中年人——刘祖民师傅。他带着一脸憨厚质朴的微笑看向我们,仿佛已候多时。说是中年人,其实他已年过六旬,但看上去最多五十来岁,腰背挺直,精神健朗,不见半分老态,只在双鬓间稍微现出点点斑白,平添了生命与岁月的沧桑与厚重。双手摊开,刘师傅声如洪钟雄浑豪迈:“走走走!喝茶去!”正欲抬步相随的我们,却又被旁边土坡上的几间简陋木屋吸引着一步一步走上去。依着这斜土坡,建着两间长长的木瓦棚,里面顺坡趴着两条三十米左右的“巨龙”,侧面分别有几个黑乎乎的洞口,人可躬身而入。刘师傅介绍,这就是烧陶罐的窑洞。那个看起来有些古旧的叫“龙窑”,已两百年左右,现在主要用来烧制烘笼钵(烘笼是印江本地一种携带方便的冬天取暖的竹编,烧制的陶钵就卡放在竹编下半部用来盛炭火。)左边较高的稍显新色的叫“阶梯窑”,在龙窑的基础上改进而成,专门烧制精品。别看这两个窑炉低矮着身子匍匐于土坡,其实,内空约有两米高,一次出窑产品三千件左右。每个窑炉分成四至五段分别供火,那些洞口就是每一段添加柴火的灶口,这样整个窑里的陶罐就可以保持温度一致并得到充分煅烧。
对于温度,刘师傅说全凭经验用肉眼观察并进行调控,从一个小孔看进去,如果里面的陶罐呈红光,则表示火候刚好,若是泛着刺眼白光,就表示温度过高,陶罐颜色就会不均匀。比如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鸡甑盖子成品,一个呈温润的麦黄色,图案线条柔和自然。而另一个则呈青绿色,图案线条有一种深嵌式的裂纹,突兀生硬,且颜色分布不均,就是由于温度过高所致。说起颜色,其实就是釉彩。刘师傅说,釉彩的产生其实源于一场“事故”:当年先祖们在烧制过程中,草木灰不经意间沾到了陶罐上,形成了一层有颜色的光滑表面,于是,釉彩就这样意外而又合理地出现了。
踏进去窑洞上方两间简陋屋子的一刹那,竟然有一种穿越的错觉,以为来到了远古。到处是灰乎乎的罐胚坛胚,粗糙鄙俗,形态各异。这是一个纯粹回归了的泥与土的世界,就好像突然置身于一个身着短褂,叉着光脚丫的粗壮野性的庄稼汉群体,让你在一种原始的气息涌动中不知所措。这是一个看不见任何现代化设施的手工作坊,所依赖的器械只有一些桶与盆,锤与棒,一些模具,几个需要用牛拉动来调和砂泥的石碾,还有几个嵌在地上的“石磨”。所有各式形状的陶器就是用这个“石磨”加工而成。加工者必须手脚协调并用:脚不停地蹬动“石磨”旋转,靠着它的惯性,用双手捋着石磨中间的砂泥团,上下左右,里里外外,均匀用力,就在这一转一捋间,形态各异的陶胚便魔术一般幡然呈现。其间,得及时拍水,水得适量,多了会让已成形的陶罐软塌,少了又会断裂。
这一转一捋的简单动作让朋友看得兴起,非要来个现场展示,还夸口自己曾做过陶罐,此乃轻车熟路。天知道一上去就把个砂泥团捋成了一个两尺来高的“高倍望远镜”,然后咕嘟一声疲软下去,活活变成一个由无数环状线条垒成的碟子。第二次尝试却拍水太多,又成功让塌下去的碟子里盛得一汪浑浊。这不,第三次尝试,觉得“石磨”转得太快,伸出脚想去阻挡,却生生把自己整个给“惯性”到磨盘上像坐海盗船一样荡悠悠晃上好几圈,吓得好一阵嚎叫。
这是一个时空被无限拉长拉慢的放大的世界。一件精致的陶罐从泥坯到出窑,需要不下三十道工序。在这期间,刘师傅在祖辈传统技术的基础上,又创新了很多精美的造型和品类。比如面前一个双手合十端然而坐的观音,便是刚刻好的盛酒器模子,与之配套的八个善财童子小酒杯模子正在雕制中。我震撼于眼前这极不和谐的情景:粗糙的双手,粗犷的脸庞,粗壮的体魄,粗陋的屋舍,粗蛮的器械,却满地满架小巧精美形态各异惟妙惟肖的泥坯。也正是这双粗糙大手所加工的一大批作品,源源不断地被省市县博物馆和很多学校收藏。目前各处收藏数量已分别达约六十件。同时,2015年还进入贵州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个原生态的手工作坊,也被授予“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传习基地”,而这双粗糙大手所传承的技艺,被贵州省政府评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这双抟着粗泥的大手,又何尝不是一双精美的艺术之手?它们用阴刻,阳刻,或者干脆笔绘等方法,让一堆生硬呆板的泥巴从此便具有了灵性,载着一段故事从远古从深山缓缓走来。
看着这屋里屋外灰乎乎的泥巴,我有点犯傻:这是黄泥巴吗?但是并不黄,反而是带着一种灰白色呀!刘师傅爽朗大笑:这可不是一般的泥,它取材于寨子后面一段特殊而又稀有的土层间,叫作“砂泥”,有着特殊的化学成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祖辈才从湖南一路迁徙一路寻找到达印江,并在印江辗转多地,最终才在朗溪镇这个叫荥家湾的半山上定居下来。刘师傅和二弟刘祖全现在是这门手艺的第七代传人,说到祖辈和渊源,刘师傅很是自豪。
如果说,刚才在作坊里是身处一个原始状态的平面图中,那么,这走下平台的一瞬间,我们则是被吸入了一个立体的陶罐部落了!陶罐花钵,陶罐茶壶,陶罐茶杯,陶罐酒壶,陶罐酒杯,陶碗,陶盆,甚至,煮饭也是用一个别致的陶罐,一股久违的稻米香随着陶盖的揭起而溢出,让人瞬间饿感十足垂涎三尺。突然,又一阵茶香缭绕着由屋外袅袅蔓延——刘师傅用陶罐茶壶给我们往陶罐茶杯里沏茶。茶叶是他自己炒制的,阵阵浓郁的香味里泛着一股淡淡的焦糊味,喝上一口,苦涩后的清凉在舌尖瞬间蔓延,眉头不自觉地紧皱又舒展,再紧皱再舒展,一如刘师傅谈起自己的技艺: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印江的陶罐市场已经被大批量生产的外来陶器所垄断,他的手工作坊变得越来越艰难。于是,他在摸索中创新,比如,他利用砂泥能煮能烧的特性,打破了传统的盛装器皿钵和罐的局限,更多地去加工养生食品的蒸煮用具——比如,鸡甑,把杀好洗净的鸡抹上佐料,直接放在鸡甑里,再把罐放进盆里蒸,蒸汽顺着甑内的四个附着的管道由下而上进入里面,然后液化沉积形成浓郁喷香的蒸汽鸡汤,在前面提到的印江十二宴席宣传活动中,刘师傅便凭着这一甑一鸡参展土司宴,获得好评。而今,这一类产品已经供不应求,他也开始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宣传销售,已有很多东西远销外地。“这虽然赚不了多少钱,但至少,祖传的手艺不会在我这代人丢掉!”豁达畅笑间,刘师傅憨厚而又乐观。
天花乱坠的臆想里,有悠悠酒香扑鼻而来,刘师傅怀抱一个圆肚子陶罐,边走边说:“自己栽的葡萄,自己酿的酒!”说着,用手指着檐外,只见葡萄架上枝枝蔓蔓纵横交错间,已经有绿光泛滥,在太阳下泫然而动。几个月后,这该又是一片浓绿海洋了!晶莹的葡萄又将与质朴的陶罐进行着一场前世今生的邂逅并产生一段醇美佳话了。“冬天,我们经常会用几个小时来慢炖牛蹄花,那一个软糯温香呀,啧啧啧!”憨厚的刘师傅冷不丁的幽默让人顿时畅想无极限。严老师眼神飘缈,酒香萦绕中妙语幽幽:“这里有酒有故事,我陶醉了!”
血红色的葡萄酒,棕褐色的陶罐酒器,敦实纯朴的饭甑,鲜花盈然的花钵,以及神龛上那常年举着串串余烬的祭祀香钵,一如刘师傅肚子里关于祖传的技艺和故事在香火延续中从古到今。啜一口酒,夹一个又长又红的泡辣椒,酒的辣,辣椒的辣,合奏了齐刷刷的一声长吸和一阵释放,仿佛刘师傅的手艺,在艰难的坚守后,终于得到认证保护后的释然。咬一口白蒿草粑粑,软糯香中浸淫馅儿的润泽,一如刘师傅脸上洋溢着的自信之光。
“来,酌酒!”刘师傅起身拿起面前的古拙酒盅。酒盅上面刻着他的一句话:“交朋结友情义长,人生品茶幸福多。”
文/徐岚
编辑/黄若佩
二审/姚曼
三审/黄蔚